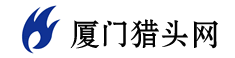埃里克•米尼克尔(Eric Minikel)和索尼娅•瓦拉巴(Sonia Vallabh)夫妇都是博士生,为了研究一种罕见的遗传疾病,他们放弃了自己原本的职业。这种病已经夺去了瓦拉巴母亲的生命,而且可能还会夺去她的生命。
安泰保险(Aetna)的首席执行官马克•贝托里尼(Mark Bertolini)曾辞掉工作,专心照料自己深受癌症折磨的儿子,后来他将这段经验运用到对这家美国大型健康保险企业的管理中。贝托里尼说:“生命短暂。”他手上带着一枚象征死亡的黑骷髅戒指。
在以上两个例子中,人们的工作动力来自于意义和目的。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不过是极端个例,大多数上班族通常都是没精打采地走进办公室,既不知道除了每天贡献那么多时间,自己还为这份工作贡献了什么;也不知道除了按部就班地工作、按时领薪水以外,自己还能从这份工作中得到什么。
这种预设的嘲讽可以理解,但未免说得太过轻巧。
在企业营销人员的美化和宣传下,关于工作目的、价值和意义的声明总是有流于空洞的风险,就像大多数使命宣言那样。当这些空话碰上关键绩效指标和奖金目标,往往被这些严酷现实撞得粉碎。
Blueprint for Better Business(我是这家机构的一名受托人)最近举行了一次会议,伦敦政治经济学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)的纳瓦•阿什拉芙(Nava Ashraf)在会上表示,企业行为如果与其宣称的理念不一致,空谈目标可能会“让事情变得更糟”。研究表明企业员工“如果将全部精力都用于应付这类说一套做一套的风气,就无法好好完成工作”。
瓦拉巴和贝托里尼赋予工作的意义实在太过崇高,看起来似乎遥不可及。在某些文化中,类似把爱带到办公室这种美国式的浮夸言辞又显得过于荒唐,很容易格格不入,受人嘲笑。拜托,请不要这么激情澎湃,我们是英国人。
这类冷嘲热讽本身非常危险。愤世嫉俗者假定所有大谈目的的组织肯定都是在撒谎,或至少隐瞒了糟糕的真相。这会令企业退回到旧式的传统做法:在一个部门做一件无可挑剔的好事——通常称之为企业的社会责任——借此暗示公司其他部门所有人,他们应该干好“真正的工作”。
在一次晚宴上,一家蓝筹公司的董事长的妻子曾斥责我,她的丈夫一直致力于实现严格的社会责任目标,却不能公布自己取得的进展,就是因为担心记者会穷追不舍,试图找出一件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。
我并不接受这样的指责。企业需要一些怀疑,以阻止它们做出见利忘义的行为。如果它们制定了远大的目标,却做不到——比如立志打造“清洁”汽车,却欺骗用来测量这些汽车有多清洁的系统——会令那些制定了明确目标的企业更难取信于人。
不过,全然的不信任会妨碍企业采取使利润与宗旨相一致的初步举措。正如Grant Thornton UK的首席执行官萨沙•罗曼诺维奇(Sacha Romanovitc)在Blueprint会议上所讲,应允许企业领导人谈论进展不顺利的地方,“而不会因此被击垮”。
个人力量在推动工作目的性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。瓦拉巴对《哈佛公报》(Harvard Gazette)表示:“我们很乐观,而且充满希望,我们相信自己正在推动世界前进。我们可以将精力投入到这里,而不用去推动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。”母亲所罹患的大脑疾病就隐藏在她的DNA里,对病痛的恐惧驱使着她和丈夫去寻找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。
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样激烈的鞭策去采取行动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必要怀着自己的全部理想投入到工作中去。这甚至并不可取。全情投入到工作中可能意味着亏欠家人朋友。但认定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,则是丧失理想、浑噩度日、自欺欺人(这一点是最可怕的)的安慰剂。那些对工作毫不在意的人,可能在家的表现会有所不同,甚至是截然相反。
只要在工作中加入一点儿目的性,那种驱动瓦拉巴和贝托里尼去工作的目的,就可以让工作更充实,上班效率更高,而且——听起来可能有些理想主义——还会让企业和整个社会变得更快乐、更人性化、更繁荣。
对最好的工作应该有意义、或最好的企业应该有目的这样的想法冷嘲热讽,本身就像一种疾病,会蛀空对企业的信任,直到其彻底垮掉。人们应该与玩世不恭作斗争,因为贝托里尼说得对,生命短暂。
厦门猎头网 厦门猎头公司 厦门猎头